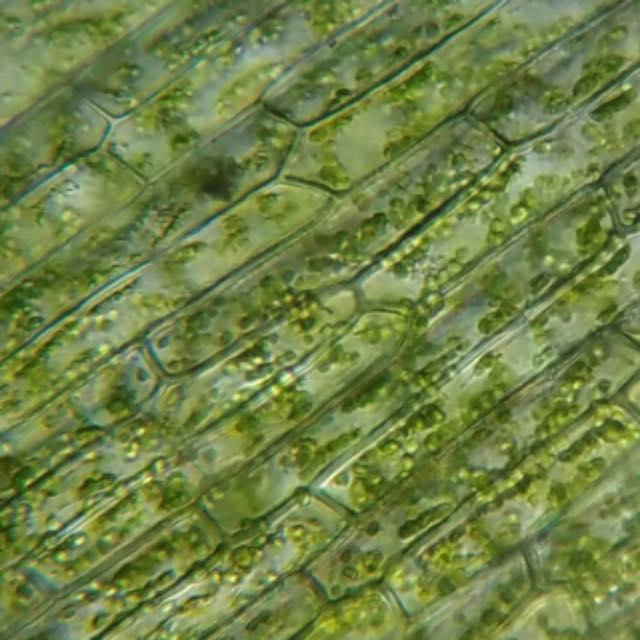小学前没上过幼儿园,偶尔奶奶休息,妈妈就把我带到单位。中午在食堂吃饭,打开饭盒,满满一碗大米饭。米是津南小站稻,白里泛青,油光锃亮。我爸蒸饭时水总是搁少,密结的饭粒儿像小人国的鹅卵石,颗颗饱满,晶莹剔透,离全熟欠个一两厘,特别有嚼劲儿,吃惯后养出铁胃,和一副好牙口。
菜盒里是成人巴掌大的瓦块鱼。鱼是鲤鱼,五斤以上的活鲤鱼不认命,挣扎着打挺,水花四溅,鱼头鱼尾朝两边来回拐,啪啪地特别生猛有劲儿,恨不能抽捕鱼人一个大嘴巴。天津人管这叫大拐子鱼,春天的大拐子出了名的好吃——可不是嘛,脾气倔,天天练着跳龙门,没跳过去,倒练出一身紧实肥厚的好肉。
烧鱼得放郫县豆瓣酱,加陈酿酱油和料酒烹,再多搁甜醋,大拐子那份不甘心就都化做香气,锅盖焖不住,咕嘟咕嘟顺着锅沿边缝往外窜。
烧熟一块块儿铲出来,因为提前过了油,鱼皮咬上去微脆的,又有点儿韧,薄薄一层裹着暗红醇厚的汤儿汁,鱼肉也入味,虽然有刺,但好吐。零零碎碎的葱姜蒜粒都酥了,也能下饭。
这样的瓦块鱼专捡中段,再加两大块儿黄亮的鱼籽,把菜盒填得瓷瓷实实——都是从家里带的。
窗口再要一份地三鲜。食堂做茄子从不削皮,和乒乓球大的本地新土豆切滚刀块儿,在油锅里炸透,呈半透明状,也不盛出来,就手扒拉到锅边,大火烧得旺,只剩点儿底油,倒黄豆酱、酱油、糖、盐。最后喷料酒,锅腾地就着了,窜起一束可以燎原的火光,又随着师傅有节奏的颠锅,很快熄灭。
临出锅前撒一大把青椒片和蒜末。送到嘴里有茄子和土豆的香软弹润。半生的青椒新鲜脆辣,又不至于抢味儿。三鲜过口,各显神通,明明不是上乘食材,却能烧出至味。
打饭的窗口前早就排起长队,没有和师傅过硬的交情,不一定能抢到。
但我妈总能打到,因为其他工友要看我吃饭。听闻我要来的叔叔阿姨,早就慷慨地把他们排到的那份让给我们。然后团团围坐在桌边,看着我妈帮我把围兜带好,铝勺递给我,一样样饭菜摆在我面前,向四周做个“嘘”的手势,对我说:“自己吃吧。”
我目不斜视,天地万物都化为虚有,只全神贯注地盯着饭盒里的美食,勺子挖到的地方稳准狠,鱼刺吐得干净利索,青椒嚼得咔嚓作响,菜汤儿搅饭更是津津有味儿,吃到最后还知道把碗底的饭渣子刮干净,这叫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四周充斥着工友们:“她怎么也不用大人喂?”、“我们孩子要是吃饭这样就太省心了”等感叹。现在回忆起来,那就是吃播的雏形,可见当前各种大胃王视频盛行,不是偶然的。
我妈得意洋洋地欣赏这一幕,对各种夸赞坦然受之,这大概是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那一代,特有的炫耀理由——一个双职工家庭有能力将他们独生女喂饱、喂好、吃得脸蛋儿红彤彤,像个早晨刚从地里挖出来的旱萝卜,鼓溜儿的脑门儿直发亮。那是计划经济刚完结时最好的时代。
我的贪吃、会吃在亲友中口口相传,串门时经我“钦点”的家常饭总被主家拿出来炫耀。
比如大姨家的鸡蛋羹,四个鸡蛋打下去,加温开水一比一搅拌均匀,上锅蒸,八成熟时掀起锅盖,铺一层西红柿和火腿片,再关火,用蒸气把那两成熥熟。出锅点几滴小磨香油,再撒把小葱花,咸香扑鼻,还带点儿西红柿的酸味儿。
颜色也好,白瓷汤碗里是娇嫩的淡黄打底,上面盛开着大红、桃粉、翠绿,和金光点点的香油花儿,又鲜亮又开胃。大汤勺蒯起来,下面滑溜溜,颤巍巍,嫩得一个气孔都没有,心急却吞不下去。拌隔夜打散的凉米饭就没那么烫了,入口刚好,连汁儿带饭,一口是一口。
素三鲜包子是大舅家的拳头产品。三月的新韭菜生得细嫩,味儿最窜,黑木耳泡发切碎,柴鸡蛋炒得老老的,用筷子搛成大块儿,早市上带皮的新鲜河虾一个个剥皮,挑虾线。这几样调成馅,里面只放盐和一点儿果油,其他什么都不用。精白面半发起来,把一个个小面团擀成大剂子,玩命儿往里填馅儿,自己家吃不讲究,不用十八个褶,粗粗捏几个就行。
面发得好,包子蒸出来特别暄软,揭锅时挨得紧,得一个个往下扯。揭完锅,满满地堆在竹簸箕里,肉头头,白胖胖,上端顶个无辜的小噘嘴儿,呼呼冒白气,像跟家里吵完架、赌气跑出来的小憨憨,憨憨大肚子里藏着绿意盎然的芳草地,特别有货。这大包子我一顿吃四个,还能搭碗绿豆稀饭。比我大三岁的表哥只能吃两个半。
我三姑家也爱蒸包子,但拿捏不好火候,皮熟了馅就烂成泥儿,馅正好时皮又发粘。三姑三姑父两口子都是事业型,不擅长下厨,冰箱里塞满速食。她家的表姐又白又瘦,总是食欲欠缺。好处是身材袅袅婷婷,穿淡绿色连衣裙,像一只冰清玉洁的宋代美人壶。走起路来分花拂柳,和旱萝卜似的我云泥之别。仙女般的表姐会翘起小指尖,调一杯荔枝味的冰镇“口维可”招待我,精致的不锈钢小勺敲击玻璃杯,打着转儿,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三姑父下班时总会捎几样凉菜,我爱吃熏鹌鹑蛋和蛇皮黄瓜,黄瓜甜辣口,脆生生的,上半截都分家了,下半截却切不断,一拈就拈起整条儿,特别好玩儿。鹌鹑蛋有点儿咸,棕黑色的蛋清紧得弹牙,有熟鸡的香味儿,又带着烧松木条的烟火气,越嚼越香,一口一个,“出溜”——就进肚儿了。
吃完赶紧下桌,齁得不行啦,不管不顾地捧起姑父的大茶缸子咕咚咕咚灌茶水,满满的一杯酽茶已经放凉了,微苦中泛着茉莉花瓣的清甜,特别解渴。三姑父在边上嘎嘎乐,夸我是食神,说那家店里这两样卖得最好,茶叶也是正兴德新进的。
不常去二姑和老姑家,但不等于没有实惠可得。老姑夫在罐头厂当业务员。近水楼台的,我家立柜顶上总是叠满没有标签的罐头。方盒的是猪肉的,长盒的是牛肉的。盒盖上别着把不锈钢小钥匙,插在盒边的一个小机关上,固定住向外卷着拧一圈,罐头就打开了,用餐刀插进去纵横着划几道,一片片挑出来,粉黄色,很少淀粉,都是纯肉粒,凝着霜样的白油,就热气腾腾的油盐花卷,油化了,变成油粒,滑入花卷的缝隙里,比现在什么培根三明治硬壳多了。
水果罐头我就喜欢山楂和菠萝的,冬天屋里火生得旺,热得人口干舌燥,看八点档电视剧时,片头曲一响,我爸就从外面窗台上拿进来镇得冰凉的玻璃罐,里面沉浮着瑰丽的色块儿,要么彤红,要么金黄。一口气逼干甜滋滋酸溜溜的水果汁,果肉则用牙签插着慢慢吃,占住嘴,省得看不懂剧情,一个劲儿提问打扰大人。因为热胀冷缩,这种真空的盖子不好拧开。老姑夫教我们的巧宗,先把瓶口用热毛巾捂捂,然后倒过瓶身,盖子朝地面使劲叩几下,再一拧,很容易就开了。但是要掌握力度,弄不好就碎了。我靠这手绝活儿在江湖上显摆到现在,在单位随手给女同事开个拌饭酱不在话下。
还有二姑的女婿——大表姐夫刚下海,做小食品批发生意。大包大包的美国开心果和海南空运鱿鱼片。塞在网兜里,每次二姑回娘家,总是拎着满满的一大袋子给我捎来,我妈本来反对我吃零食,怕影响吃饭,但被特别叮嘱是好东西,别糟践了,于是每天给一小把,揣口袋里边玩儿边吃。我奶奶养的大黄猫也喜欢鱿鱼片,没少从我这蹭。
说起这只大黄猫,和我真是哥俩好,我吃的东西除了水果冰棍儿它不喜欢,其它它都爱;它吃的除了邻居伯伯养的活鸽子我不敢下嘴,剩下我们都能共享。我奶奶去早市买菜时,光顾的一家鱼贩子总给她留小鲫瓜,回来用小洋炉子架上平底锅,切两片五花肉煸出油,把鲫瓜子丢进去煎煎,加小碗水熬白,给我盛一碗汤,剩下半碗连鱼带肉调棒子面煮成粥,倒进猫碗儿里,我和猫咪吧唧嘴的声音震天响,进院就能听见。
她还养了两只花母鸡,圈在黑漆漆的杂物间里不见天日,可是争气,每天都下蛋。用白搪瓷缸子煮了,早上十点剥给我吃。我吃一个整个的,和一个蛋清,留一只蛋黄给大黄猫。过了几年,母鸡老了,不下蛋了,我奶奶总说要把它俩处置了。有一天我午觉醒来,我妈给我指碗橱上一盆炖鸡,说是奶奶给端过来的——她终于把那两只鸡给宰了。
我盯着那只缱绻着的鸡脑袋,和支棱着的粗糙的鸡爪,想起它们生前咕咕咕碎嘴子的样子,没来由害怕起来。第一次因为“吃”被吓得哇哇哭嚎。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看鸡头和鸡爪子。我妈中年以后半真半假地开始信佛,和尚讲法时我也跟着看了一会儿,提到“三净肉”的说法,虽然对宗教无感,然于我心有戚戚焉,虚伪地自我安慰是个有善根的人。转念一想,我奶奶和大黄猫兄弟若是活过来,知道我有这样的念头,怕是又要笑死过去。
我大伯那会儿在一家国营百货商店当售货员,卖地毯,算高级柜台的柜员,收入很体面。商店离奶奶家近,他每天都回来吃午饭,拐进胡同时会在巷口右手边的康乐冷食店给我捎一盒“美登高”——很出名的冰激凌牌子,这两年也赶着怀旧风重出江湖,但与儿时的味道不太相同了。
那时我们管这个叫冰点心,我喜欢绿色哈密瓜味儿的,上面一层精致的轧花,装在透明小方盒里,点缀着鲜红的果干粒。我大伯腰上拴着的钥匙扣是一只老铜铃,我在院门口玩儿,远远就能听见他进胡同的动静。其时不管手里在忙什么,都赶紧抛下,飞奔出去迎接他,他会张开双臂一把将我揽起高举过头顶,让我猜今天冰点心放在哪个兜里。
我特别爱我大伯,笑起来既爽朗,对我又大方。他只有我堂哥一个儿子,但又喜欢女儿,所以一直管我叫“大爷的闺女”,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小时候总叮嘱我:“大爷的闺女大爷疼,大爷的闺女疼大爷,等大爷六十六时,你给大爷割刀肉。”我问他割完肉怎么吃,他反问我你想红烧还是清炖?我说要是五花肉就红烧,排骨就清炖,炖完蘸酱油。我们爷俩就那块肉讨论了一次又一次。而他真的六十六岁那一天,我甚至没有去看他。从他中风之后到现在,我只去过他家一次。他躺在床上假装不认识我,眯着眼睛问:“谁?你是谁?”
我像小时那样滚在他身侧,没大没小地拽他耳唇,又薅他头发,说:“我是你的大侄女,像我这么耐人儿的你没见过几个,别给我装。”他憋不住乐了,过了一会儿收起笑容,喃喃道:“我侄女爱说话了,比小时候开朗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道:“没有,大爷,我小时候可爱说话,是个话痨,您记错了。我后来不说话是因为心情不好。”
他别过头,不再看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