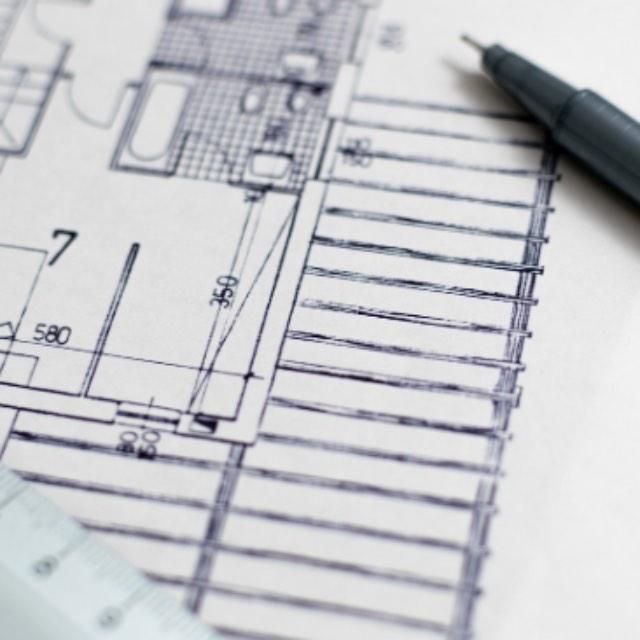问题在于“一样”和“证明”上。
举个例子,群(group)。
群的视角上,你能分辨
和
吗?显然不行。它们是同构的。但是这是同一个群吗?从集合论的视角来说不是。因为用具体的编码展开来之后,我们知道
,然后
,
本质上是一个二元运算,虽然写起来麻烦,但是差不多是一个包含了形如
形式的元素作为其唯一元素的集合。别的不说,
和
用某种纯集合的编码展开之后,里面使用到的大括号的数量都不一样。那么,在这种语境下,至少作为集合,它们大概显然是不同的。
类似地,当你说“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完全的一样可言。
数学里面我们在意的,可能是是否有一个 bijection,一个 isomorphism,当然有些时候对于 iso,我们要求的是某种更好的性质,比如说 naturality。但是往往都是两个东西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关联。
这里有若干个层次,最细的当然是:我这个蓝色的 token 和那个不一样,我每次感受之间的区别,我个别记忆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蓝色的感受不仅仅是感受本身,而且自带了时空标签。当然这里的“空间”是什么多少有点暧昧:一方面,我们的视觉是二维的,三维是大脑脑补出来的,另一方面,我们习惯用三维的光影去补足色彩上的区别,实际上对于一个人来说,要像画家一样正确读取出自己视域中对象的“真实”颜色还是有点困难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考虑最朴素的情况,比如说,现在我的电脑桌面上有三四个蓝色的图标,虽然时间上都是此时此刻,但是引入了“空间”之后能刻画出这种区别。当然了,实际上当数量超过三个(如果你觉得不够可以再加,问题不大)的时候,我已经要数数了,甚至一眼关注到的图标可能只有两个(同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主观的角度上,真正的同时的空间其实是一个很局限的情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比较大的电脑屏幕上玩过找颜色和其他点颜色不同的游戏,如果我真的能在“同时”的意义上读取所有的点,那肯定能更快一些,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需要扫视,当然手机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我也觉得其实我不可能关注一整块手机屏幕,而总是以二分或者四分的方式逐一扫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蓝色的 qualia 的 token 都装在一个贴了时空标签的盒子中。我甚至不需要看盒子里面的内容,看到时空标签我就知道是不同的。(这样说当然有一点粗鄙,因为在渐变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很难判断到底一个色块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纯色色块。利用 qualia 的表述或许稍微绕过了对比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没有完全绕过去。所谓的对比的问题就是,“同样”的蓝色色块,在被不同颜色包裹的情况下,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
再粗一点就是,感受和记忆的区别,或者说,impression 和 idea 的区别。总之就是亲身体会到的部分,和脑补想象的部分的区别。
进一步,我们可以强行说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相当于把盒子外面的时间标签丢了,只比较盒子里面的东西,以及,盒子是谁的。
这个类比延续下去就是,你似乎想要找一个比较的方式:我们不比较盒子外面的标签,只比较盒子里面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从原则上来说,我看不到你的盒子里面的东西,你也看不到我的盒子里面的东西。所有神经生物学上的东西都是“模仿”:我找一个第三方,闭着眼睛复制一个盒子里面的对象,然后传递给我:但是我、你、第三方都根本看不到盒子里面的对象是什么,只有将这个对象交给我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它是什么。你说这个地方复制没错——然而谁知道呢?我们复印文件的时候也总会说复制没错,但是拿到手上的时候可能是打印机里面的虫子也复印进去了。但是如果我永远都没有办法 access 原件,单凭你这样一说,我怎么知道对不对?何况这里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一个或者两个复印件的问题:所有用来校准的东西都是我这一侧的复印件,我只能比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能比较它是不是“绝对”的那个东西。我如果能拿到原件,我可以说你复印错了,但是我永远都不可能拿到原件。所有东西都是一开始就是我这一侧的东西。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复印的机理是什么,或许你用的墨盒本身一开始就装错了,或许你用的纸张表现不出来某些细微的纹理,或许一开始就没有原件,复印机其实是打印机,这里的很多参数其实是即兴发挥出来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经生物学手段的复制或许更像是操纵电脑,但是我们拿到的盒子里的东西则是打印出来的成品。什么时候我能真的确定一种关联性?不是科学家在那里操纵我的大脑,而是我自己在操纵我的大脑,然后感受会发生什么。——如果哪一天这个技术实现了,至少我可以确立某种从第三人称操作到第一人称操作的主观权威性,但是我们也不缺这个:你看,我知道要去哪里找一个蓝色的东西,打开知乎,按钮是蓝色的。我很“确定”这个蓝色和昨天看到的蓝色是一样的。何种意义上确定?我不知道。
当我们说有一个从 A 到 B 的函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 f(a) = b ——但是问题来了,并不是 a = b,而是 f(a) = b。而且这里我们总可以隔离开来,事实上“等于”是非常暧昧不清的东西。哪怕 A 是 B 的子集,我们除了显然的嵌入之外,也总有一些不显然也不自然的操作。比如说对于从 {1,2} 到 {1,2,3} 的嵌入,是把 1 映射为 1,把 2 映射为 2。但是,至少从集合的范畴来看,如果我们把 1 映射为 3,把 2 映射为 1 呢?其实也没有问题,只不过这个时候,这个函数虽然依旧能起到类似于 {1,2,3} 的子集的作用,但是这个地方挑选出来的子集更像是 {1,3} 而非 {1,2} 了,我们经历了一个这样的 factor through:
,
,
。事实上,任何一个二元集都可以以某种方式作为 {1,2,3} 的“子集”(因为 SET 中的对象只在乎 size,所有二元集是“同构”的),从函数的观点看,子集的本质仅仅是一个单射罢了,真正起到作用的东西并不是原来那个集合里面的元素,而是实际上的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的“比较盒子里面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游戏。甚至,我们很难把这个游戏拓展到历时的情况下:我们的短期记忆就这么点容量。而除非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否则我们很难以非常鲜活的方式回忆起它们。而且对于人来说,回忆的本质不是在硬盘上读取东西,而更像是解压或者根据一些线索再创作,假设我锚定的蓝色是知乎的图标,哪天知乎的图标颜色改了,或者我换了一个显示器,那我回忆的时候就可能会根据这个新的蓝色来重构我脑海中的画面。我们的记忆其实是糊的。
又比如说,考虑到显示器的色差之类的问题:我们只有在一个比较短的,有对比的情况下能判断出来两个显示器的色差。在经过了充分长的时间之后,我们就会习惯新的显示器,而忘记过去的显示器和现在这个显示器的色差。哪怕某些人真的还记得,也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比如说,手机屏幕没换,起到了中介的作用,或者,因为新显示器对于某两个颜色的区分度没有原来好之类的,而不是说记住了那个绝对的颜色。类似性质的例子还有换眼镜:我们很快就会忘记旧的佩戴感,而习惯新眼镜附带的时空扭曲。哪怕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扭曲在,但是我也不知道要如何修正它。我当然可以再戴回原来的眼镜,但是这个时候和原来的观感依旧不同,因为我“不习惯”了。只有当我再重新习惯原来的眼镜之后,才有可能说重新获得戴原来的眼镜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我要怎么比较这个感觉,和习惯了新眼睛之后的感觉呢?没法比较。我只能笼统地说“习惯”或者“不习惯”。
你“有一个感觉”,这个说法没错;你可以“用一种私人的方式指向它”,这个也没错——如果这里的“私人性”体现在“你感受到它了,但是我没有”上面——那么,这个“私人”不过是你“有一个感觉”的同义反复罢了。但是,这一部分中某些不可言说的内容称不上语言游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可以依赖的标准。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说,从语言或者规则或者方法论的层面逼近的过程是很相似的:如果你不知道他人的情况,那么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所谓的你觉得你知道,知道的标准是什么?是你的记忆?你的记忆是不可错的吗?
我拿出一张红色的色卡,指着它说,“黄色。”你说:“不对,这是红色。”我:“啊呀不好意思咬到舌头了~”
——你看,我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可能犯错。但是错误不止这一种,我也可能找错色卡:
我想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红色的,于是去拿红色的色卡,结果不小心拿了黄色的色卡去比较。这个时候我指着一个红色的对象说它不是红色的,因为它和色卡不同。又指着一个黄色的物件说它是红色的,因为它和色卡相同。直到你向我指出:“你拿的是黄色的色卡!不是红色!”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利用记忆中的色卡去比较感受到的色块,别人(当然包括你自己)没有办法做一个仲裁。我没有办法走到你的大脑里面说你是取错色卡了还是指绿硬说蓝。同理,别人也没法在你做对的情况下判断你是“真的对了”,还是“错了两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某些“对错”被瓦解掉了。
除非你把这个规则用公开可以理解的语言记录下来,但是一旦记录下来了,这个游戏的就不由你一个人说了算了。比如说,你想要依赖某个现实中的物件来对比蓝色——那这个物件进入语言游戏的方式,并不是作为你内心中的盒子中的对象这种方式,而是一种更加外在,公开的方式。哪怕你的视觉和别人不同,只有你能判断出两块大家都觉得没区别的颜色的物件,最后的结果也是落在你会判断出不同的能力上,而不是一个完全私人的“我感觉到了不同”。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实验设计来判断你是否真的知道不同,而不需要我能感受到这种不同。这就像是红绿色盲的人虽然自己是红绿色盲,但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发现别的人能多分辨出来一些颜色。(但是,难道他没有获得他看到的颜色和别人看到颜色不同的证明吗?那么在相同意义上,他也可以(借由他人的帮助)“证明”两个人看到了相同的颜色)
这并不是在否定内在感觉,但是它并不是标准。又或者说,能力从一开始就不是标准。我借助内在感觉获得了分辨颜色的能力,这种感觉和红绿色盲的感觉显然是不同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我们在能力上的不同,但是反过来,我们不能断定因为我们能力相同,就有相同的内在感觉。然而,如果用数学的说法,我们把别的东西模掉(类似于
),只考虑一个基于能力的商空间,那么两个能力相同的人在这个商空间中自然处于同一个点中,但是这个点,是由原空间中的点构成的等价类。
这就像考试一样:我们不知道你怎么做出来的,我只能知道我是怎么做出来的,但是既然你做出来了,那么我们相信你有这种区分能力。但是最后的标准并不是落在“我有能做出来这道题的感觉”或者“我的灵光一现”上,而是落在你写下来的答案上,不仅仅你可以批改,大家都可以批改。你觉得你会做,除非你做出来了,否则屁用没有。当然这里会有意愿的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说,如果做对的奖励足够大,你宣称自己会,但是又做不出来,那别人可以大致判断你不会。阅卷人看到答案,知道你会做,但是不需要阅卷人自己会做。当然,如果阅卷人自己会做题,他也可以不看参考答案就判断你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说的就是正确的。他有达到标准的能力,于是他不需要借助标准答案,而可以自己得到那个东西。仅此而已。光是一个“我感觉你是错的”和“我感觉我能做出来”一样,本质上屁用没有。
这个地方本质上是一个语法问题:当“一样”的标准本身涉及到,比如说,时空标签的时候,那么你的两个不同的蓝色的记忆,自然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标签不同。就像是你的电脑上可以存两个内容一样的文件,但是却存在不同的文件夹下面。一个是 2022-06,另一个在 2022-07。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要提供某种更粗的东西,也即,允许某种谈论我的蓝色和你的蓝色是否相同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则必须需要某种转换和比较。但是当你谈论这种转换和比较的时候,就类似于说,这个显示器上的蓝色是不是就是那个显示器上的蓝色——我们看到不同,但是依旧回答“是”,理由不是那个绝对的色块,而是“它们在显示同一张图片”。
和电脑不同,我们的大脑并不是量产的,或许个别外设可以简单替换,比如说眼角膜或者晶状体或者什么的,我不确定视网膜的替换是不是有可能,但是这些充其量都是外设。如果我们具体的编码不同,而且不存在一个简单的转换关系,那么自然地,我和你看到的东西就不同。但是这个不同根本没有意义,因为这里说到底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排除了相同的可能性:诚然,一个正常人可以说,如果有一个物理上和我完全一样的人,那么如何如何——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物理上的完全一样是做不到的;而第二个问题则是对于利用 happy accident 这种说辞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时候类似于沼泽人的困难,我们很难说它有 mental object。而如果不是说“物理上完全一样”,那很有可能光是一些配件上的差别都会使得两个人的视觉观感有区别,比如说视锥细胞数量上的微妙差异,比如说晶状体内部的混浊。
总的来说就是,所谓的“证明”和“一样”是绑定在一起的。你的“一样”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就预先将“证明”不可能化了。但是反过来,如果就按照日常的标准,比如说,用正常视力和红绿色盲或者红绿色弱作为标准,显然我们可以说两个人的视力水平一样。所谓的一样,说粗鄙一点,就是“某个人不会将 A 色当成 B 色”。(当然详细一点还有不同颜色之间的远近亲疏的问题,也即,色弱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依旧可以还原成形如“某个人会否将 A 色当成 B 色”的形式,只不过 A 和 B 要再多一些例子罢了。)
而这也就足够了。
当然,mad scientists 可能会说我们可以不断逼近一个核心的地带。比如说,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更换一个人的脑组织,然后问他是否有区别(然而我想象不出来有什么电脑可以这么莽地热插拔硬件同时还保留了文件在 cache 中不受损坏)。
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因为人脑本身是带有透镜的。我们的“视觉”并没有那么干净。我们在看到东西的时候,不仅仅有一个自下而上的,纯输入的部分,也有一个基于大脑的,从上而下的筛选,输入的东西再多也没用,我们不可能“看到”所有的细节,至少在一个瞬间不能。这使得我们看到或者注意到的部分,以及它们呈现的方式,不是“原汁原味”的。甚至一些认知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会预先把看到的内容做一个分类,贴上标签,比如说,在压力测试下,一个人可能会把黄色的圈和红色方块汇报成红色的圈和黄色的方块:也即,他“看到”了圈和方块,“看到”了红色和黄色,但是却不小心搞错了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小心把圈 link 到了黄色上。也即,对于大脑来说,形状和图形才是基本的“储存原子”而不是作为整体的视觉输入。——这也是符合常识的,只有我们想到了,才有可能看到。面对一些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质”的东西,哪怕我们看到了,也会忽略掉。就像是下水道井盖上的米老鼠耳朵,只对于那些知道这个 meme 的人有用。
在这种意义上,你去单独筛选一个孤零零的玩意儿出来,就和在数学里面问“如果我把 2 删掉会怎么样”一样——那原来的 2 就要映射成现在的 3。又或者,如果你是指所有包含 2 的字符都删掉,那就是进制转化。无论如何,单独一个 2 没有任何意义,它作为自然数的功效在于,它是 1 的后继以及 3 的前驱。从范畴论的角度上来说,
和
没有区别。它们都是 SET 的 terminal object。
另一个可能有点糟糕的比喻是,你以为你读到的“蓝色”是数据,可能你读到的只是一个压缩过的编码,或者一个指针:如果没有背后的那一整套东西,你还原不出来需要的玩意儿。你此时此刻记录下来的,个别神经结构,未必能够放到别人身上,甚至未必能够重新塞回这个人自己身上。这就像是说,你拆了一台 Google 的服务器,放在那里放了一个月,然后再装回去——我觉得大概率会出错吧。或许有某种完全不会出错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有点困难。有些粗鄙的物理主义者把物理决定心灵想得太简单粗暴了,仿佛任何一个内存条都可以随便热插拔到另一个主板上正常工作一样。然而即便计算机没有任何非物理的地方(这里指“灵魂”或者“心灵”),这样做也行不通啊。哪怕不是电脑,就算是一架飞机,你也不能在飞行过程中更换其中某些零件吧。
同时,人脑本身也有塑造的部分,也就是说,越是多看,你的感受性就会越强,你能分辨出来的细微之处就会越多。(比如说喝酒,而且考虑到经验知识作为外在的语境,本质上就和围绕在色块外面的颜色一样,会影响到你的体验,也就是说,我甚至可以主张这里的 qualia 都不再相同了。)
这也就使得很多时候,我们要谈论一样的时候,只能在一种差不多的意义上谈论。想要那种精确的东西,算是奢望吧。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