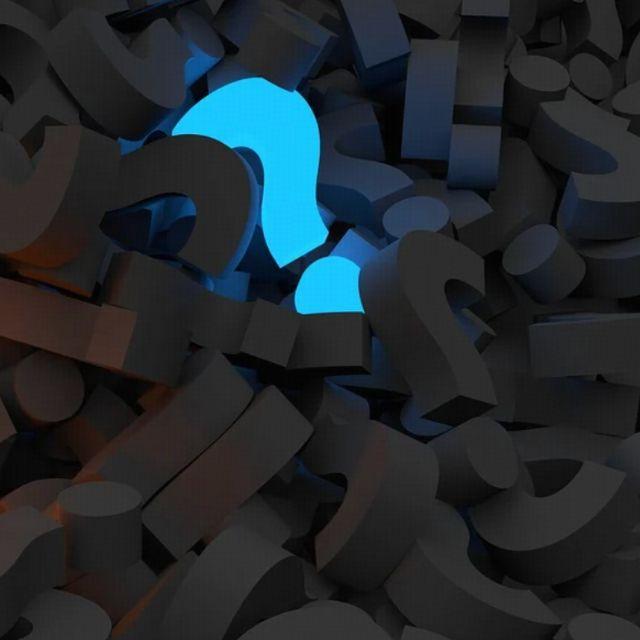那天一个人逛翠湖,看见湖边公园坐着两个算命的瞎老头儿,傍晚已经落了,锻炼的大部队还没来,是一天之中生意的淡季。
那老头,一个安静地在发呆,不知道想些什么,另一个拿一只收音机,正在听相声。
说相声的嗓门儿老大,讲一些又旧又逗的梗,情境里还录了观众的笑声,高高浮在公园上空的云朵里。
还有一回,在海南某个大排档,一行人点了鲜活虾蟹水产,等待上桌。
人群里远远听见有二胡声,都是破碎的片段,喜庆洋溢,音符不时从嘈杂里蹦出来,零落成泥的高兴。
走近了,才发现是两个人。
年纪相仿的中年人,一个盲了眼睛,一个视力完整的牵着他,到桌前,拉一段二胡,说几句漂亮话,伸手,要一点钱。
我摸了半天,摸到几块现钞,递过去。
“好人一生平安。”那盲人说。
“不客气,祝您一切都好。”我说。
“您声音真好听啊,我再给您拉一段吧。”他忽然抬起手,又拉了一段曲子,尾音又美又凉。
“谢谢,这歌儿真好听,谢谢。”我说。
然后饭菜上桌,他们也走了。
我是个共情能力泛滥的人,总是先别人一步涌上耻感与悲欢。但后来我告诉自己,不要急着施舍自己的同情。
没有谁比谁高一等,也没有谁天然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欢愉。
我们能做的,就是制造更多的乐趣,然后互换高兴。
那两天我都挺高兴的,为不同境遇的人都有那么多高兴的时刻而高兴。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